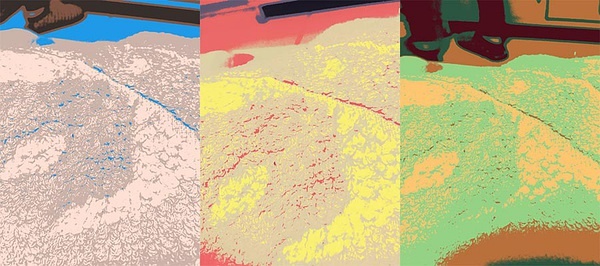
冬天终于过去了,灰蒙蒙的天有望短暂放晴一段时间了。今天的气温高的有些离谱,只好翻出了一件薄外套穿着出门。无意间在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以为早已丢失的耳塞。耳塞捏在手里有种特殊的质感,线也没有搅成一团,轻轻一抖就乖乖分开了。这一切都预示着某种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
迫不及待想立刻试一下。想想离上次用它听歌应已过去半年了。陈粒的《历历万乡》在这个温暖干燥的上午显得有点沧桑了。下一首。《易燃易爆炸》。这个好,可是这首歌太短,干脆单曲循环吧。
我把手机塞进口袋里,公交车站就在眼前了,114来了,跑了两步赶在车门关闭之前跳上了车。突然,一个问题闯进我的脑子,我要去哪里?这个问题太突然,打乱了我顺利成章的动作和思路。赶紧跑到车厢中间看线路表,期望从中找到一丝线索。奇怪的很,这些站名我虽然都认识,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里,似乎我从来没坐过这辆车。当然,也无从看出我的目的地到底是哪一站。
额头有点冒汗,天太热了。鼻塞似乎变严重了,讨厌的感冒还没好彻底。感到一阵虚脱。慌忙找了个座位坐下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告诫自己要冷静,可以坐下来慢慢分析。
–– 盼我疯魔还盼我孑孓不独活
这歌已经放了几遍了,怎么现在才唱第一句?我不自然的注意到耳塞里传来的音乐。不行,还是先想想我要去哪里。是「海淀桥北」吗?这个地方似乎有点印象,据说这里有一片树林,在夜里会发出神秘的呼喊声,像远古野人的呐喊。不是这里,野人与我无关。
–– 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
我是谁?
这个时候想这个问题可不对。
车门开了,海淀桥北到了,我犹豫了一下,没有下车。我注意到这站上来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。她的脸过于苍白,没有血色。手想必是冰凉的。这个女人与这个天气不搭。倒不如说与这个世界不搭。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她竟在我旁边的座位坐下了,我感到喉咙发紧。头晕。
–– 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
“请你把车窗打开好吗?”她竟然对我说话了,而且还是我能听懂的话。不合理,她应该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。她是谁,她要去哪里,会是和我去同一个地方吗?也许是回家呢。这么说来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。头晕。
“好的”,我在想上面那些问题时,这句话已脱口而出。
我把车窗打开一条缝,风吹进来,吹在我脸上。
虽说今天暖和,可毕竟现在还是三月,风吹在额头上还是有些凉。我可能是又出汗了,额头传来滑腻冰凉的感受,像我想象中蛇的触感。叫人恶心。头晕。
“你脸色很难看,而且出了很多汗。你没事吧?”红衣女人问我。
“哦,我得了感冒,有点虚弱而已,不碍事的。”
”那么要不要在下一站下,去医院检查一下?”
下一站?下一站是哪里?似乎有一站靠近医院的。该死,想不起来是哪一站。
“不… 不用了吧,是小毛病,而且也快好了。”
“最近流感严重,你还是小心为好。”
你是谁?我生病关你什么事?我突然变得有些恼怒,是弱点完全暴露在陌生人面前那种因无助导致的恼羞成怒。
“…”
我那样想着,却什么也没说出口。
–– 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
女人竟然拉着我的手下车了。她力气实在很大,我无法反抗。我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汗还在往外冒。恶心。头晕。
“这是哪里?”,我问。
“你不是发烧了吧,这个地方不认识吗?”
“以前似乎来过,可确实想不起来是哪里”,这种感觉很奇怪,明明有印象,却记不得名字。
“是医院,过来吧。”
她好像没有挂号,直接拉我进了一个诊室。我虽然不记得这是哪里,但去医院要挂号这样的生活常识却没有忘掉。
“医生呢?”,我环顾四周,诊室空无一人。
我应该是发烧了,眼睛发烫,额头仍然保持着那种冰凉滑腻的恶心感。我又感到头晕,不得不扶着旁边的床坐下来。
床单是刺眼的白色,与女人的红衣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不协调。不协调的女人。我一惊。这个女人到底是谁?我为什么要跟她来这个医院?我在做什么?我今天早上原本是要去哪里?
“想起来要去哪里了吗?”,女人突然发问。
我脸一下子红了,心思被人看穿。嘴里发干。恶心。头晕。
我支支吾吾。
“其实你今天就是预约了来这里看病的。”
我瞪大了眼睛。眼前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,怎么会与她约好了来看病呢?
“那么我得的是什么病?”,我也许受惊吓过度,反倒冷静一些了。于是抛出尖锐的问题期望她露出马脚,以便于我尽快明白眼前发生的事。
“你得了间歇性失忆症。”
再次震惊。
“什么… 什么病?”
“就是说你会时不时的失去记忆,部分记忆。生活能力、常识等你不会忘记。”
好像说对了呢。
这么说来我真的得了这种病么?也许我的耳机根本没丢过也说不定。也许我真的跟这个女人预约了看病也说不定。但无论怎么看,这个女人与这个世界都不协调。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
“你是谁?”,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出这个问题。
“我是谁不重要,你要信任我。”
得到了让人丧气的回答。
“那么… 我该怎么办?”,我决心不刨根问底了,听天由命。
“需要抛弃你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,方能治愈。”
说了莫名其妙的话。
“我… 现在实在不想与人讨论人生啦、哲学啦。请告诉我具体怎么办?”
“这不难理解。躺下吧。”,她指了指我屁股底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床。
我竟顺从的躺下了。
她走过来,伸出惨白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,我看到露出的手臂也是惨白的。出人意料的温暖。额头感觉到温暖。让人昏昏欲睡。
“没事,忍耐一下。”
她说着,手就伸进了我的头里。一阵钻心的疼痛。我看不到她在对我的脑袋做什么。疼的晕过去了。
不知过了多久,醒来。
–– 怨我百岁无忧还怨我徒有泪流
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就是耳塞还在响,还是《易燃易爆炸》。第二件注意到的事是我还坐在114路公交车上,身边没有什么红衣女人。第三件注意到的事是车窗开着,风吹在额头上没有了那种冰凉滑腻的蛇的触感。我突然想起来我要去哪里了,鼻塞似乎减轻了很多。我晃晃脑袋,无比轻松。
我望向窗外,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,无比清晰。那个红衣女人,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她也许是把脑子从我头颅里取了出来,想让我余生做一个无脑之人吧。
